母親,,我最敬愛的母親,,她去逝快到十年了。 她雖然以離我們遠(yuǎn)去,,到遙遠(yuǎn)天國的那方了,;但她的音容相貌永遠(yuǎn)活在我的心中。
我的母親命苦,,她本是生長在離縣城不到五公里遠(yuǎn)長江南岸的沙溪村古家山人,。 聽母親說,她早年父母雙逝,,是母親把兩個弟弟拉扯成人,,“長兄為父,長姐為母”,,家中的擔(dān)子落在母親的肩上,,母親在家中排行老大。 母親十七歲經(jīng)媒人之說嫁給我父親,。 那時候我父親家生活非常貧窮,,經(jīng)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,吃不像吃,,穿不像穿地度日子,,一家人擠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的土胚房里,風(fēng)霜露宿的土胚房成了深邃的眼睛,,白天陽光折射,,晚上在被窩偷窺一眼,能看到月亮星星,。 母親一直在家跟地主幫長工“放羊喂豬”之類雜活,,有時連飯都吃不上,稍有怠慢遭人辱罵,。
饑寒交迫的生活慢慢地重見天日,。母親是一個堅強的女人,,看著兩個弟弟長大成人,加上族里的大幫小湊,,蓋起兩間新土胚房,,是給兄弟倆的新房。 想當(dāng)初,,我的父親母親結(jié)婚也沒有舉行什么婚禮儀式,,就直接跟隨我的父親去我們家了。母親共生育兒女七個,,兩個姐姐,,一個妹妹,四個兒子其中,,老三和我是孿生,,我是四個兒中排行老幺,父親和母親給我們孿生取了卓號化名(大毛),、(細(xì)毛)至今都還有人這樣稱呼……
父親,,我還沒有叫過他一聲父親,就連他的身影我都沒記住,,在我印象最深處,,只有那么一點點,父親就去逝了,。遺體停在“關(guān)堂”房里,,父親的遺體放在關(guān)堂屋正中間,關(guān)堂屋生了兩堆篝火,,是給嗩吶吹鼓手們?nèi)∨玫?,他們是母親邀請來給父親告慰亡靈的。 有很多人頭上纏繞著雪白的白布跪在父親的靈柩前,,凄涼的呻吟哭泣,,泣不成聲。 哭泣聲隨嗩吶鼓聲蕩漾在關(guān)堂屋上空,,燒香的,、燒陰錢的、燒煙火的,、放鞭的,,彌漫整個場地上空。 我和孿兄還無知地在父親靈柩前玩,。
父親的遺體出葬那天早上,,是二姐背我去的,孿兄是大姐背去的,。父親的遺體埋在“土地堂”的背面,,后靠廟背坡大山根基,前向南方,,左邊山形落差,,右邊是一口十幾畝大的水塘,用來灌溉水田的,。 父親的埋擇地“椅子”形,。
母親說:父親年輕時是大隊的大隊長,兼職大隊民兵連長,,是當(dāng)時下隊里包隊干部,,整個蓮花洞公社,八個大隊都知道“張連長”,,家喻戶曉,。去縣城開會,徒步幾十公里,,兩頭都黑,。他為人正值,學(xué)習(xí)上進,,工作負(fù)責(zé),,偶爾帶公社領(lǐng)導(dǎo)秦大兵書記和八大隊大隊長趙正舟,來我家作客,,都贊他是一個“工作狂”,。這就是我的父親張炳成。
在母親講述著父親生前故事的時候,,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父親,,是一個多么熱愛工作事業(yè),祗衹奮進超越自己的強人,。 父親的肺結(jié)核病俞越俞烈,,到了垂死掙扎的邊緣,無情的病魔纏著他往鬼門關(guān)拖,,他臨別時拉著母親的手,,一張病入膏肓的睿臉,就象水土流石似的樣子,;坑洼不平,,油干燈盡的境界,眼里泛起顆顆催人淚下,,難分難舍的依戀淚珠……充滿了渴望與萬個不舍,,千個不離的場景,父親說話很遲頓,,就像一座大山壓抑在他身上似的,,吞吞吐吐說道:“我走了不要緊,,你不要哭,要堅強的活著,,把七個孩子養(yǎng)大成人”,, 話音剛落,父親撒手西去,,享年35歲,。
父親含笑九泉,撒手西去,。七個孩子的擔(dān)子沉壓在母親一個人的肩上,,這個擔(dān)子不是一般人能挑的,何況面對的是一個弱女子呢,? 隨著時間的推移,,以悲痛化為力量。 土地改革了,,家家戶戶分田分地了,,光靠分得的田土就有十幾畝田地,那個年代沒有錢買化肥,,只能用自制的農(nóng)家肥,。 母親是一個心思縝密、堅強不屈的人,,她有一套嚴(yán)管教風(fēng),,說一無二,丁是丁卯是卯的家法訓(xùn)服人,,以“黃金棍”下出貴人為標(biāo)準(zhǔn),。 母親雖然沒有讀過好多年書的人,但買進賣出的經(jīng)濟帳,,她都能算得出來,。面對家庭大的大、小的小,,如何管教不聽話的兒女,;首先,微笑待人說服教育,,講故事打比喻的形式教育人,,實在不聽話那就使用家法“黃金棍”教育人。
母親逢人就講,,黃金棍下出貴人,,就這樣,我們在母親的黃金棍下個個長大成人,接人品對,,安居樂業(yè),。 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七姊妹扯成人,母親心酸的青春歲月褶皺,,時間渲染她的鬢發(fā),;母親的背就象河邊的楊柳樹彎彎溝地水面,好像在撫摸女兒們頭似的,! 母親那一雙結(jié)實的手成滿了厚厚的老繭,是為了女兒們個個成家立業(yè)的真實寫照,。 雛形的鳥兒翅膀以硬,,卻各奔東西,留下年邁的母親守護家園,。 母親沒有跟四個兒子,,卻選擇大女家,大女孝順有佳,。這也是令母親倍感欣慰的了,。
作者張登云:315記者攝影家網(wǎng)會員,沂蒙網(wǎng)特約記者,,中國公益在線記錄者,。
315記者攝影家網(wǎng),張登云,《我的父親母親》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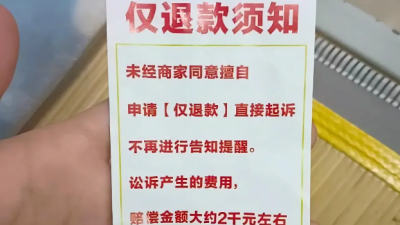

 “護眼臺燈”亂象調(diào)查
“護眼臺燈”亂象調(diào)查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“AI打標(biāo)”背后有哪些隱患,?
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“AI打標(biāo)”背后有哪些隱患,? 救命的醫(yī)療設(shè)備,,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?
救命的醫(yī)療設(shè)備,,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? 原價上千元“貴婦霜”網(wǎng)店賣不到百元
原價上千元“貴婦霜”網(wǎng)店賣不到百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