嫁妝,,是女子出嫁時(shí)娘家陪送的財(cái)物,,亦稱“嫁資”“妝奩(lián,,梳妝用的鏡匣)”等。在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,,嫁妝于婚姻意義重大,。一般來說,它在女子出嫁時(shí)是必不可少的,,無論家庭貧富,,都須盡力籌辦,。嫁妝的多少常常影響到婚約的締結(jié),豐厚的嫁妝往往可以使女性取得更高身價(jià),。在清代,,嫁妝給家庭及社會(huì)帶來了一系列影響,如助長社會(huì)奢靡之風(fēng),,導(dǎo)致婚后奩產(chǎn)糾紛等,。
一、清代嫁妝的種類
在清代,,嫁妝大體可分為生活用品和不動(dòng)產(chǎn)兩類,。生活用品是嫁妝最基本的組成部分,主要是衣物首飾和日用器具,。衣物首飾做嫁妝,,可以從最直接的層面體現(xiàn)出新婦之“新”,并且這種“新”不僅要體現(xiàn)在婚禮上,,還將一直延續(xù)到她結(jié)束“新婦”狀態(tài)為止,。
清代學(xué)者瞿兌之的《杶(chūn)廬所聞錄》中,記載了一位貧婦的嫁妝:“貧人無他長物,,止銀簪,、耳環(huán)、戒指,、衣裙,,寥寥數(shù)件而已?!苯诵扃娴呐拖蛩麛⑹隽似涞軏D的嫁妝:“布衣三十事,,為棉襖、夾袴,、棉單,、半臂、圍裙,、裹腿,,今有千張皮(碎皮紉成)之襖一,已為絕無僅有,?!保ā吨倏呻S筆》)這兩位婦女嫁妝中衣物首飾較為簡單,若富貴人家女兒出嫁,,則會(huì)陪送大量衣物首飾,,數(shù)量多的甚至足夠穿到去世。
一、清代嫁妝的種類
在清代,,嫁妝大體可分為生活用品和不動(dòng)產(chǎn)兩類,。生活用品是嫁妝最基本的組成部分,主要是衣物首飾和日用器具,。衣物首飾做嫁妝,,可以從最直接的層面體現(xiàn)出新婦之“新”,并且這種“新”不僅要體現(xiàn)在婚禮上,,還將一直延續(xù)到她結(jié)束“新婦”狀態(tài)為止,。
清代學(xué)者瞿兌之的《杶(chūn)廬所聞錄》中,記載了一位貧婦的嫁妝:“貧人無他長物,,止銀簪,、耳環(huán)、戒指,、衣裙,,寥寥數(shù)件而已?!苯诵扃娴呐拖蛩麛⑹隽似涞軏D的嫁妝:“布衣三十事,,為棉襖、夾袴,、棉單,、半臂、圍裙,、裹腿,,今有千張皮(碎皮紉成)之襖一,已為絕無僅有,?!保ā吨倏呻S筆》)這兩位婦女嫁妝中衣物首飾較為簡單,若富貴人家女兒出嫁,,則會(huì)陪送大量衣物首飾,,數(shù)量多的甚至足夠穿到去世。
衣物首飾之外,女家一般還要陪送被褥,、家具等日用器具,。在清代的黑龍江地區(qū),男家要事先準(zhǔn)備好“被褥各二,,及箱柜,、梳匣”等日用品,提前送往女家,,“俟女家送奩至男家時(shí),,攜以俱至。女家所增者,,尚有洗衣盆,、手巾、胰子(肥皂)等物”,。(徐珂《清稗類鈔·婚姻類》)此即由兩家共同預(yù)備婚后生活用品,,再以嫁妝的形式由女家發(fā)往男家。這些婚后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大到箱櫥,,小到燭臺(tái)、馬桶,,與衣物首飾一起組成全副嫁妝,。
除了生活用品,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還陪送店鋪,、土地,、宅院等不動(dòng)產(chǎn)?!肚迨犯濉ち信畟鳌酚涊d:桐鄉(xiāng)濮氏富而無子,,其女的嫁妝中“田宅、奴婢,、什物皆具”,。巨額的嫁妝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。如吳三桂之婿王永康,,婚前家境敗落,,漂流無依,婚后則窮極奢侈,,儼然廁于縉紳之列,。
二、清代嫁妝的規(guī)模
嫁妝的多少隨女家貧富程度而定,,差別很大,。清代最為隆重的嫁妝當(dāng)屬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妝奩。如光緒帝大婚時(shí),,皇后的嫁妝共二百抬,,其實(shí)際價(jià)值很難估算,。此次大婚總共花費(fèi)白銀五百五十萬兩,其中皇后的妝奩占不小的比例,。
官員家庭的嫁妝也十分可觀,。清人吳熾昌《客窗閑話》記載一位白姓侍衛(wèi)“因愛女遠(yuǎn)離,盛備奩具,,媵(yìng,,陪嫁)以婢仆百余,雇群艘,,由水路行,。運(yùn)奩之日,自京至通,,四十余里,,絡(luò)繹不絕于道者,翌日始畢”,。近人吳汝倫的外祖父馬魯迂在蜀地為官,,吳汝倫母親出嫁時(shí)“裝貲甚盛”。不過由于官員們追求“廉潔”的名聲,,對(duì)女兒嫁妝的實(shí)際內(nèi)容往往比較隱諱,,很少見到確切的記載。
與官員的態(tài)度相反,,商人在陪送時(shí)則愛“炫富”,。多數(shù)商人之女的嫁妝都有銀兩記載,毫不隱諱,,甚至夸大,。如有人為昆山學(xué)者龔煒之子與某湖商女做媒,特意說明“奩資可得數(shù)千金”,;又如,,山西洪洞人韓承寵娶晉商亢氏女,“奩金累數(shù)萬”,;江寧某商人在義女出嫁時(shí),,“奩贈(zèng)十萬金,使成嘉禮”(《清稗類鈔》),。
不過,,史料中的“千金”“數(shù)萬”,往往用以形容嫁妝之多,,而非具體數(shù)額,。康熙帝曾恩賞41位因貧困而無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兩銀子,以籌備嫁妝,。乾隆帝亦曾下旨賜宗室貧困者每人“賜銀一百二十兩以為妝費(fèi)”,。可見,,100兩銀子左右的嫁妝,,在清前中期應(yīng)為一份比較體面的嫁妝。
晚清時(shí)嫁妝的數(shù)額有所變化,。曾國藩一向治家節(jié)儉,,認(rèn)為“吾仕宦之家,凡辦喜事,,財(cái)物不可太豐,,禮儀不可太簡”。大女兒出嫁時(shí),,曾國藩“寄銀百五十兩,,合前寄之百金,均為大女兒于歸之用,。以二百金辦奩具,,以五十金為程儀”。為防止講排場(chǎng),,他一再叮囑“家中切不可另籌錢,,過于奢侈”。(《曾國藩全集·家書》)從曾國藩給女兒準(zhǔn)備的嫁妝估算,,當(dāng)時(shí)200兩銀子的嫁妝應(yīng)是既體面又不奢侈。
如果將物價(jià)上漲的因素考慮在內(nèi),,晚清200兩銀子的價(jià)值與清前期的100兩銀子差不多,。可見,,清代中等規(guī)模嫁妝的標(biāo)準(zhǔn),,在100兩至200兩白銀之間。一二百兩銀子的花費(fèi),,對(duì)官僚縉紳和富商大賈而言,,根本算不上負(fù)擔(dān),但貧困之家溫飽尚難解決,,更談不上為女兒陪送體面的嫁妝了,。許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時(shí)出嫁,或找不到合適的配偶,。面對(duì)這種情況,,一些宗族義莊出資為族中貧困女子置辦嫁妝。道光、咸豐年間,,常熟鄒氏義莊規(guī)定:族中貧困之家嫁女給銀五兩,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濟(jì)陽義莊規(guī)定嫁女貼錢六千,。(《明清以來蘇州社會(huì)史碑刻集》)但這還不是筆者所見的清代嫁妝的最低標(biāo)準(zhǔn),。
清人歐陽玉光妻蔡氏,家貧,,“將嫁,,宗族周焉,得錢三千有奇”,。這錢蔡氏不忍帶走,,最后留給老父用以維生。(《清史稿·列女》)三千錢的嫁妝可謂簡陋,,但根據(jù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者的研究,,這對(duì)于貧困農(nóng)民而言,常常相當(dāng)于一年的家庭總收入,,貧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見,。
三、引發(fā)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問題
嫁妝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屬于消耗品,,其價(jià)值隨著時(shí)間流逝而遞減,;而其中的土地、店鋪,、宅院等不動(dòng)產(chǎn),,則可能隨時(shí)間的推移而增值。然而在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中,,后一類嫁妝卻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問題,。
首先,這些不動(dòng)產(chǎn)不能隨著女子的出嫁而遷移,。特別是如果締姻兩家相距較遠(yuǎn),,婚后無論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,還是土地和店鋪的管理都極為不便,?;诖耍宕S多家庭在陪嫁不動(dòng)產(chǎn)時(shí),,都會(huì)預(yù)先考慮到距離問題,。清初吳三桂受封平西王,駐云南,,而女婿王永康為蘇州人,,吳三桂“檄江蘇巡撫”,,在蘇州“買田三千畝,大宅一區(qū)”作為女兒的嫁妝,;雍正年間,,年羹堯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,年羹堯在濟(jì)寧買田19頃,,作為女兒的奩田,;乾隆年間,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,,他斥資萬兩,,在附近為其女置買莊田四處。這幾個(gè)例子說的都是高官顯貴,,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離遙遠(yuǎn),,不得不將嫁妝中的土地房屋變賣。
其次,,店鋪,、土地等作為嫁妝,很容易造成經(jīng)濟(jì)糾紛,。店鋪與土地同樣不能遷移,,但店鋪更需要日常的經(jīng)營與管理。嫁妝中的店鋪,,通常會(huì)出現(xiàn)兩種情形:一是將店鋪的所有權(quán),、經(jīng)營權(quán)全部轉(zhuǎn)移到女兒女婿手中,改由男方直接經(jīng)營,。如京城崇文門王氏“以質(zhì)庫(當(dāng)鋪)作奩資”,,將女兒嫁與一舊家子?;楹蠓蚱抻忻?,王女罵道:“吾父以數(shù)萬金之質(zhì)庫舁汝不為薄?!保ㄓ狎浴秹?mèng)廠雜著》)該質(zhì)庫是以嫁妝的形式全權(quán)轉(zhuǎn)贈(zèng)給女婿,由他直接經(jīng)營管理并獲取收益,。二是店鋪繼續(xù)維持原有的經(jīng)營管理模式,,出嫁女只獲得收益權(quán)。如林則徐的父親在為兒子們分家時(shí),,考慮到已婚的長女,、次女、五女嫁妝單薄,,決定將龍門口四間店面分給三人,,以補(bǔ)從前之不足,。
嫁妝中的土地,即奩田問題更為復(fù)雜,,并非像有些學(xué)者所認(rèn)為的那樣,,奩田屬分割產(chǎn)權(quán):所有權(quán)在娘家,使用權(quán)在夫家,。奩田是一種特殊的土地讓渡形式,,既區(qū)別于土地買賣,因?yàn)殡p方并不涉及金錢交易,;又區(qū)別于土地的完全轉(zhuǎn)移,,因?yàn)榕彝鶎?duì)奩田做出種種限制。奩田權(quán)屬糾纏不清,,容易引發(fā)經(jīng)濟(jì)糾紛,,下面舉兩個(gè)案例加以說明。
案例1:道光四年(1824),,四川巴縣朱太貴起訴姐夫?qū)⑵浣愕膴Y田隨意變賣,。朱太貴之姐嫁給赤貧無業(yè)的陳以謙為妻,朱家“所贈(zèng)妝奩服飾不少”,,其姐生子陳慶美后,,娘家又追贈(zèng)奩田一份,但規(guī)定,,田業(yè)不準(zhǔn)陳家私當(dāng)私賣,,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給陳慶美作為學(xué)費(fèi),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為陳慶美將來婚娶的費(fèi)用,。(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)
此案例中,,奩田合約明確規(guī)定,陳以謙父子不僅沒有土地所有權(quán),,而且對(duì)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嚴(yán)格限制,。此合約由“親族鄉(xiāng)戚”作證,即產(chǎn)生了法律效力,,陳氏父子不得違背,,否則可能導(dǎo)致訴訟。
案例2:雍正六年(1728),,劉連俸的祖父將一塊土地贈(zèng)與姑爺張九安以作奩業(yè),,當(dāng)時(shí)說明“世守業(yè)不問,倘有典賣,,業(yè)仍還劉姓”,。但嘉慶五年(1801),九安夫婦去世之后,,九安之子張世文“忘恩負(fù)義”,,“將業(yè)私售”,。(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)
這里,女家在陪送嫁妝時(shí)亦明確規(guī)定:如果男家世代守業(yè),,則女家對(duì)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過問,。然而,一旦男家變賣奩田,,女家即要將其收回,。也就是說,男家擁有對(duì)奩田的所有權(quán)和使用權(quán),,但沒有出售權(quán),。可見,,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對(duì)奩田的權(quán)利,,不能簡單地劃分為使用權(quán)和所有權(quán)。
作者簡介
毛立平,,女,,1974年生,山西太原人,。歷史學(xué)博士,,中國人民大學(xué)清史研究所副教授,主要從事清代社會(huì)史,、性別史研究,。著有《清代嫁妝研究》(獨(dú)著)《19世紀(jì)中國婚姻家庭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透視》(合著)等,發(fā)表論文十余篇,。
除了生活用品,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還陪送店鋪,、土地,、宅院等不動(dòng)產(chǎn)?!肚迨犯濉ち信畟鳌酚涊d:桐鄉(xiāng)濮氏富而無子,,其女的嫁妝中“田宅、奴婢,、什物皆具”,。巨額的嫁妝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。如吳三桂之婿王永康,,婚前家境敗落,,漂流無依,婚后則窮極奢侈,,儼然廁于縉紳之列,。
二、清代嫁妝的規(guī)模
嫁妝的多少隨女家貧富程度而定,,差別很大,。清代最為隆重的嫁妝當(dāng)屬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妝奩。如光緒帝大婚時(shí),,皇后的嫁妝共二百抬,,其實(shí)際價(jià)值很難估算,。此次大婚總共花費(fèi)白銀五百五十萬兩,其中皇后的妝奩占不小的比例,。
官員家庭的嫁妝也十分可觀,。清人吳熾昌《客窗閑話》記載一位白姓侍衛(wèi)“因愛女遠(yuǎn)離,盛備奩具,,媵(yìng,,陪嫁)以婢仆百余,雇群艘,,由水路行,。運(yùn)奩之日,自京至通,,四十余里,,絡(luò)繹不絕于道者,翌日始畢”,。近人吳汝倫的外祖父馬魯迂在蜀地為官,,吳汝倫母親出嫁時(shí)“裝貲甚盛”。不過由于官員們追求“廉潔”的名聲,,對(duì)女兒嫁妝的實(shí)際內(nèi)容往往比較隱諱,,很少見到確切的記載。
與官員的態(tài)度相反,,商人在陪送時(shí)則愛“炫富”,。多數(shù)商人之女的嫁妝都有銀兩記載,毫不隱諱,,甚至夸大,。如有人為昆山學(xué)者龔煒之子與某湖商女做媒,特意說明“奩資可得數(shù)千金”,;又如,,山西洪洞人韓承寵娶晉商亢氏女,“奩金累數(shù)萬”,;江寧某商人在義女出嫁時(shí),,“奩贈(zèng)十萬金,使成嘉禮”(《清稗類鈔》),。
不過,,史料中的“千金”“數(shù)萬”,往往用以形容嫁妝之多,,而非具體數(shù)額,。康熙帝曾恩賞41位因貧困而無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兩銀子,以籌備嫁妝,。乾隆帝亦曾下旨賜宗室貧困者每人“賜銀一百二十兩以為妝費(fèi)”,。可見,,100兩銀子左右的嫁妝,,在清前中期應(yīng)為一份比較體面的嫁妝。
晚清時(shí)嫁妝的數(shù)額有所變化,。曾國藩一向治家節(jié)儉,,認(rèn)為“吾仕宦之家,凡辦喜事,,財(cái)物不可太豐,,禮儀不可太簡”。大女兒出嫁時(shí),,曾國藩“寄銀百五十兩,,合前寄之百金,均為大女兒于歸之用,。以二百金辦奩具,,以五十金為程儀”。為防止講排場(chǎng),,他一再叮囑“家中切不可另籌錢,,過于奢侈”。(《曾國藩全集·家書》)從曾國藩給女兒準(zhǔn)備的嫁妝估算,,當(dāng)時(shí)200兩銀子的嫁妝應(yīng)是既體面又不奢侈。
如果將物價(jià)上漲的因素考慮在內(nèi),,晚清200兩銀子的價(jià)值與清前期的100兩銀子差不多,。可見,,清代中等規(guī)模嫁妝的標(biāo)準(zhǔn),,在100兩至200兩白銀之間。一二百兩銀子的花費(fèi),,對(duì)官僚縉紳和富商大賈而言,,根本算不上負(fù)擔(dān),但貧困之家溫飽尚難解決,,更談不上為女兒陪送體面的嫁妝了,。許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時(shí)出嫁,或找不到合適的配偶,。面對(duì)這種情況,,一些宗族義莊出資為族中貧困女子置辦嫁妝。道光、咸豐年間,,常熟鄒氏義莊規(guī)定:族中貧困之家嫁女給銀五兩,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濟(jì)陽義莊規(guī)定嫁女貼錢六千,。(《明清以來蘇州社會(huì)史碑刻集》)但這還不是筆者所見的清代嫁妝的最低標(biāo)準(zhǔn),。
清人歐陽玉光妻蔡氏,家貧,,“將嫁,,宗族周焉,得錢三千有奇”,。這錢蔡氏不忍帶走,,最后留給老父用以維生。(《清史稿·列女》)三千錢的嫁妝可謂簡陋,,但根據(jù)經(jīng)濟(jì)史學(xué)者的研究,,這對(duì)于貧困農(nóng)民而言,常常相當(dāng)于一年的家庭總收入,,貧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見,。
三、引發(fā)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問題
嫁妝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屬于消耗品,,其價(jià)值隨著時(shí)間流逝而遞減,;而其中的土地、店鋪,、宅院等不動(dòng)產(chǎn),,則可能隨時(shí)間的推移而增值。然而在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中,,后一類嫁妝卻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問題,。
首先,這些不動(dòng)產(chǎn)不能隨著女子的出嫁而遷移,。特別是如果締姻兩家相距較遠(yuǎn),,婚后無論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,還是土地和店鋪的管理都極為不便,?;诖耍宕S多家庭在陪嫁不動(dòng)產(chǎn)時(shí),,都會(huì)預(yù)先考慮到距離問題,。清初吳三桂受封平西王,駐云南,,而女婿王永康為蘇州人,,吳三桂“檄江蘇巡撫”,,在蘇州“買田三千畝,大宅一區(qū)”作為女兒的嫁妝,;雍正年間,,年羹堯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,年羹堯在濟(jì)寧買田19頃,,作為女兒的奩田,;乾隆年間,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,,他斥資萬兩,,在附近為其女置買莊田四處。這幾個(gè)例子說的都是高官顯貴,,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離遙遠(yuǎn),,不得不將嫁妝中的土地房屋變賣。
其次,,店鋪,、土地等作為嫁妝,很容易造成經(jīng)濟(jì)糾紛,。店鋪與土地同樣不能遷移,,但店鋪更需要日常的經(jīng)營與管理。嫁妝中的店鋪,,通常會(huì)出現(xiàn)兩種情形:一是將店鋪的所有權(quán),、經(jīng)營權(quán)全部轉(zhuǎn)移到女兒女婿手中,改由男方直接經(jīng)營,。如京城崇文門王氏“以質(zhì)庫(當(dāng)鋪)作奩資”,,將女兒嫁與一舊家子?;楹蠓蚱抻忻?,王女罵道:“吾父以數(shù)萬金之質(zhì)庫舁汝不為薄?!保ㄓ狎浴秹?mèng)廠雜著》)該質(zhì)庫是以嫁妝的形式全權(quán)轉(zhuǎn)贈(zèng)給女婿,由他直接經(jīng)營管理并獲取收益,。二是店鋪繼續(xù)維持原有的經(jīng)營管理模式,,出嫁女只獲得收益權(quán)。如林則徐的父親在為兒子們分家時(shí),,考慮到已婚的長女,、次女、五女嫁妝單薄,,決定將龍門口四間店面分給三人,,以補(bǔ)從前之不足,。
嫁妝中的土地,即奩田問題更為復(fù)雜,,并非像有些學(xué)者所認(rèn)為的那樣,,奩田屬分割產(chǎn)權(quán):所有權(quán)在娘家,使用權(quán)在夫家,。奩田是一種特殊的土地讓渡形式,,既區(qū)別于土地買賣,因?yàn)殡p方并不涉及金錢交易,;又區(qū)別于土地的完全轉(zhuǎn)移,,因?yàn)榕彝鶎?duì)奩田做出種種限制。奩田權(quán)屬糾纏不清,,容易引發(fā)經(jīng)濟(jì)糾紛,,下面舉兩個(gè)案例加以說明。
案例1:道光四年(1824),,四川巴縣朱太貴起訴姐夫?qū)⑵浣愕膴Y田隨意變賣,。朱太貴之姐嫁給赤貧無業(yè)的陳以謙為妻,朱家“所贈(zèng)妝奩服飾不少”,,其姐生子陳慶美后,,娘家又追贈(zèng)奩田一份,但規(guī)定,,田業(yè)不準(zhǔn)陳家私當(dāng)私賣,,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給陳慶美作為學(xué)費(fèi),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為陳慶美將來婚娶的費(fèi)用,。(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)
此案例中,,奩田合約明確規(guī)定,陳以謙父子不僅沒有土地所有權(quán),,而且對(duì)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嚴(yán)格限制,。此合約由“親族鄉(xiāng)戚”作證,即產(chǎn)生了法律效力,,陳氏父子不得違背,,否則可能導(dǎo)致訴訟。
案例2:雍正六年(1728),,劉連俸的祖父將一塊土地贈(zèng)與姑爺張九安以作奩業(yè),,當(dāng)時(shí)說明“世守業(yè)不問,倘有典賣,,業(yè)仍還劉姓”,。但嘉慶五年(1801),九安夫婦去世之后,,九安之子張世文“忘恩負(fù)義”,,“將業(yè)私售”,。(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)
這里,女家在陪送嫁妝時(shí)亦明確規(guī)定:如果男家世代守業(yè),,則女家對(duì)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過問,。然而,一旦男家變賣奩田,,女家即要將其收回,。也就是說,男家擁有對(duì)奩田的所有權(quán)和使用權(quán),,但沒有出售權(quán),。可見,,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對(duì)奩田的權(quán)利,,不能簡單地劃分為使用權(quán)和所有權(quán)。
作者簡介
毛立平,,女,,1974年生,山西太原人,。歷史學(xué)博士,,中國人民大學(xué)清史研究所副教授,主要從事清代社會(huì)史,、性別史研究,。著有《清代嫁妝研究》(獨(dú)著)《19世紀(jì)中國婚姻家庭的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透視》(合著)等,發(fā)表論文十余篇,。
(編輯:月兒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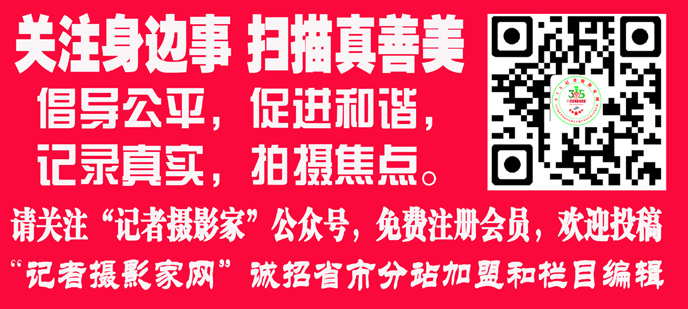







 “護(hù)眼臺(tái)燈”亂象調(diào)查
“護(hù)眼臺(tái)燈”亂象調(diào)查 AI賬號(hào)成起號(hào)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“AI打標(biāo)”背后有哪些隱患,?
AI賬號(hào)成起號(hào)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“AI打標(biāo)”背后有哪些隱患,? 救命的醫(yī)療設(shè)備,,如何淪為個(gè)人提款機(jī)?
救命的醫(yī)療設(shè)備,,如何淪為個(gè)人提款機(jī)? 原價(jià)上千元“貴婦霜”網(wǎng)店賣不到百元
原價(jià)上千元“貴婦霜”網(wǎng)店賣不到百元